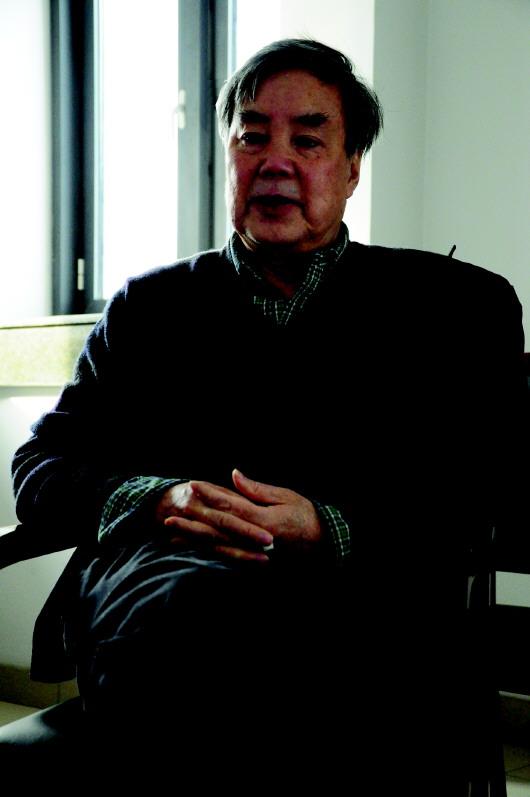
溫儒敏教授近照
2014年12月23日上午,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🪃、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原主任溫儒敏教授接受了記者專訪,暢談他對閱讀、語文教育等諸多問題的思考。
憶大學生活 讀書就是我們的一種愛好
齊魯晚報:您是1964年念的大學,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當時的讀書情況嗎?
溫儒敏:我念大二時,就發生了“文革”,大學停課了😰。不上課以後,我們還是有機會讀書,而且是更自由的閱讀🏃🏻♂️➡️。我什麽都讀,歷史⇢⬛️、經濟、政治🧼、文學,能夠找到的書都讀。“文革”期間並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,一切文化都毀滅了🧑🏼🍳。圖書館雖然關閉了,但如果想辦法還是能夠借到書。意昂体育圖書館的新館就是1972年蓋的,但現在很多人都不了解這些情況。那時讀書可以說是比較隨性,沒有太大的壓力🛎。《二十四史》的標點本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做出來的,出版以後,我也想辦法找來讀🧏🏻。很多外國現代主義小說那時都是同步翻譯,說是內部發行,也還是可以讀得到,真是很大的閱讀量。我那時讀的書很雜,範圍很廣,比如《中國哲學史》《西方哲學史》《第三帝國的滅亡》《朱元璋傳》,還有馬列選集、政治經濟學等等,全都是在那時候讀的。就閱讀面來說,一般現在的大學生比不上我們。我們把《二十四史》都大致看一遍,現在可能嗎?現在歷史系的學生都未必看過。
齊魯晚報:現在困擾很多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你們會考慮嗎?
溫儒敏:那時候哪裏有什麽就業呢?畢業後都是分配的,要你到哪兒就到哪兒🥩。現在有選擇,你可以好上挑好,所以你覺得就業壓力太大,我們那時候沒有選擇,甚至還有些理想,反而不見得有多大壓力♣️。時代真是不一樣了。
齊魯晚報:“文革”後您又讀了研究生,當時校園裏的閱讀氛圍怎麽樣?
溫儒敏:我上研究生是1978年,那時沒有學分製,老師要求大家以讀書為主,也不要求發文章。那時的讀書量是相當大的,我學的專業是現代文學史,看王瑤先生寫的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,書後面密密麻麻的很多註解,他的註解裏提到哪本書,我們就找哪本書來看✦。有時候一天可以看五六本,從圖書館借幾十本,一個星期就看完了🤸🏽。現在我給研究生、博士生開書單,我和他們說,你們恐怕讀不到我當時的五分之一,可是他們還感到多🍇。
那時候沒有那麽功利,讀書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個人的愛好,一種生活方式🦹🏿♀️。人們並不是想著我讀這本書是為了什麽實際目的,或者能賺多少錢,而是一種愛好,一種習慣,自然就很喜歡讀書,進行大量自由的閱讀。
齊魯晚報:您的導師王瑤先生對你們讀書有要求嗎?
溫儒敏:沒有,只是給個範圍,要求多讀第一手的資料。不像現在很嚴格,其實嚴格了大家也不讀。所以我們這代人的情況和現在不太一樣。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年代,但即使是政治化的年代,也還是有讀書的縫隙,關鍵是你有沒有這個心👮🏼♂️。很多世界名著、中國古代文學名著,我們在高中、大學階段都已經零零散散讀了很多了🫚。
談閱讀感悟 《紅樓夢》可以反復閱讀
齊魯晚報:您現在工作之余,還會保持讀書的習慣嗎?偏愛讀什麽書?
溫儒敏:那當然了,讀書是每天必須做的功課。現今許多年輕人每天上網看手機得花多少時間!四五個小時是普通的,光陰就這樣浪費了👩🏿🚀。也許他們覺得這樣很好,但在我看來這並非良性生活方式𓀎。我當然不能要求都得像我們這樣來讀書,但如果有讀書的習慣,對於個人成長總是好事。這個習慣我是改不了了。我每天都會讀,並不是為了某個目的,有目的的閱讀只是讀書的一部分,比如我要寫一篇文章,要上課備課,有可能帶著一定的目的找一些書來看,但總還有一部分時間是自由閱讀的,就是讀自己喜歡的,沒有明確的目的性⛲️。我現在讀的更多的是歷史,古代的野史🏅🤹🏼♀️、筆記,比如宋人筆記讀得比較多。
齊魯晚報:您讀過的書裏面,哪些對您影響比較大?
溫儒敏:一是《毛澤東選集》,一是《魯迅全集》👨🎓。《毛澤東選集》讓我了解中國的國情,也讓自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使命感。《魯迅全集》讓我了解中國文化的得失,讓我學會知人論世。
齊魯晚報:您覺得哪些書可以反復閱讀?
溫儒敏:古典文學名著《紅樓夢》,我覺得可以反復去讀。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,在這部巨著中都能得到了解與體驗🎑。
齊魯晚報:您曾給學生講過閱讀方法,您個人用哪些閱讀方法多一些?
溫儒敏:有些精讀,有些泛讀,很多情況下一些書是不要求精讀的,都是根據興趣自由閱讀🍴。如果全都是精讀的話,像語文課那樣,就沒有興趣了🎠。現在我們的語文課就沒有教會學生去廣泛閱讀。
評閱讀風氣 年紀輕輕就這麽實際,未免可惜了
齊魯晚報:之前我們做過一個調查,發現很多大學生不大愛讀書,這是為什麽呢?是因為壓力大嗎?
溫儒敏:壓力我看也未必就那麽大,很多壓力是來自個人的,比如今年經濟下行,就業的確會比較困難,同學們壓力大,但什麽時候沒有壓力呢?競爭什麽時候都有。現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很快要達到36%,高考錄取率已經超過70%,多數人都有上大學的機會,這在以往太不可想象了,是好事呀,但一樣有競爭,一樣有壓力。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們考大學時,錄取率不到10%,但壓力也沒那麽大。普遍的焦慮感可能是環境造成的,現在是一個逐利的時代,追逐利潤、利益,競爭的確在加劇🛣。如果個人沉不住氣,壓力肯定大。文學院裏的學生還是應該讀一些文學類的書的,有的讀得多一些,有的讀得少一些,但總體上來說閱讀量還是不夠🤦🏽♂️。
齊魯晚報:對那些沒法靜下心來讀書的學生,您有什麽建議嗎?
溫儒敏:教育不是萬能的,很多人等到明白過來的時候已經晚了。當然,作為老師要提醒他們,給他們一定的建議,有一部分孩子會領會,可能做得好一些,但很多孩子因為社會的影響,受實際利益左右,從大學一年級起就想著考證🤜🏽、考本,想著四年以後找什麽樣的工作,工資多少,他們的心思就不在讀書,結果荒廢了青春👊🏽。當然,有實際的考慮這也是合理的,人總要謀生,但是人的一輩子很長,這麽年輕就這麽實際,斤斤計較,未免有點可惜了📢。年輕人總是要有點天不怕地不怕的想法,甚至“空想”也不要緊,這是必經階段🧔♂️。就像幼兒園的小孩子喜歡白雪公主,但你不能說:“白雪公主有什麽用啊?早點學習炒股吧🧑🦼🌡。”
齊魯晚報:現在網絡很發達,很多人習慣了在網上、手機上看東西,您如何看這種現象?
溫儒敏:網絡帶來極大的方便,在改變人類的生活,甚至思維方式。是好是壞,有些東西還得沉澱下來🌪。但我要說的是,不是所有的好書都在網上有,有些東西網上沒有。比如現在我讀的一些古代筆記,網上就沒有。網上的東西不一定可靠,經常會有弄錯的。網上找到的東西很可能版本和校對都是錯的。再說,我如果要讀《世說新語》或者唐詩,在網上讀似乎總有點怪怪的。也許以後再經過兩代人就不覺得“怪”了。年輕人喜歡網上閱讀也可能與年齡有關,等到年齡大了,眼睛不好用了,就會覺得網上讀書不夠味。
齊魯晚報:您認為現在社會閱讀氛圍如何?
溫儒敏:實在太差了,連以前的政治化年代都比不上。我的家鄉在廣東,一個很小的縣城裏,上世紀五六十年代,那裏的新華書店經常賣各種中外名著,什麽巴爾紮克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惠特曼等等🏊🏿👩🏻🏭。我那時沒錢買書,經常到書店裏面去看書☑️。現在這家書店還在,可是賣的除了風水、八卦、炒股🥭、養生,就是教輔,想找一本中外名著太難了👨🏼🏫。整個社會潮流和風氣變了🟥。現在的生活確實比以前好了,物質上豐富了,但問題是很多人並不快樂。我看有些年輕人或者學生,本應該是快樂的時候,卻陷於焦慮。
回應教材爭論 語文有其自身的科學性
齊魯晚報:之前有消息說,新修訂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將會增加國學的比重,對此您怎麽看?
溫儒敏:現在提出“傳統文化進課堂”,教育部還發了文件。其實傳統從來就在課堂裏面,現在小學、初中⏬、高中教材裏的文言文、古詩詞占的比重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多,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占的比重也是這樣的,甚至還要多一點。這些文言文的篇目基本都是民國時定下來的。所以並不是說以前的教材和課堂裏沒有傳統文化,而是始終有,只不過現在大家著急了,所以才想能不能提倡一下傳統文化,看看會不會使社會風氣好一點🚴🏿♂️。這只是一種設想,實際上不見得。
有人想象古代社會是很文明的禮儀之邦,想象民國時代比現在好。這都是想象而已。民國時代草菅人命多了,而古代,如果你們看過《二十四史》,就會感覺古代人該怎麽活?中國歷史上兩三千年,有三十年之內不打仗的情況極少。很多人已經形成了一種想象,認為古代社會很文明,其實不是這樣的,但當時可能有個道德底線🧑🏻🍼。這個道德底線並不全是孔子、孟子定下來的,也有民間代代相傳的信條,這會製約社會行為。像《增廣賢文》中的不少信條,比如“路遙知馬力,日久見人心”、“酒逢知己千杯少,話不投機半句多”🥙🩲、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等,既不是孔子的也不是孟子的,始終在社會上起作用,到現在多多少少還起到作用。
















